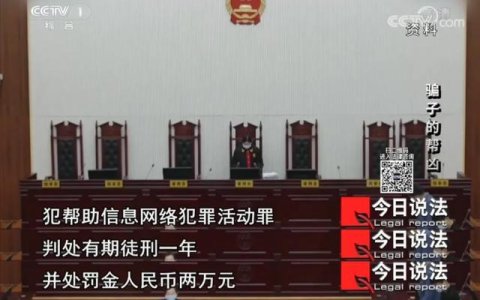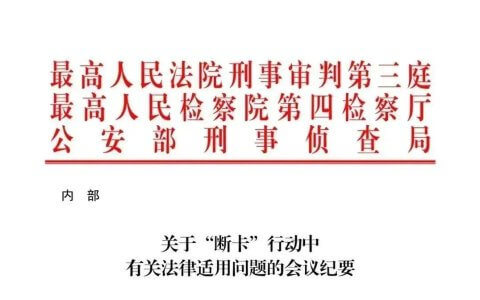二、帮信罪“明知”的理解与认定
【背景材料】
案例3:2020年11月,被告人石某因贩卖电话卡被公安机关教育训诫,公安机关告知其相关电话卡会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活动。石某被训诫后继续收购他人电话卡并转卖牟利,获利6万余元。经查,上述部分电话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但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人未被抓获到案。
案例4:2020年9月,被告人张某通过网络找到一份帮他人看管GOIP设备(用于境外人员拨打境内电话的中转设备)的工作。张某按照上家指示架设GOIP设备,将电话卡插入设备后每日看管,根据上家指示更换设备中无法使用的电话卡,并通过聊天软件每小时向上家报送数字“1”表示一切安全;若上家超过1小时未收到报送的“1”,则该窝点将予以废弃。同时,张某还负责为上家收购电话卡。张某表示其知道该GOIP设备被用于境外人员拨打境内电话实施违法犯罪时使用,但具体如何实施及实施何种犯罪并不清楚。经查,插入该GOIP设备的相关电话卡被用于网络诈骗及网络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但具体行为人未被抓获到案。
争议焦点
被告人石某、张某对被帮助对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主观上是否需要明知具体犯罪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等?何种情形下行为人已不再是帮信罪的犯罪主体,而是与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人构成共犯?
情况介绍——任素贤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对帮信罪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帮助对象利用银行卡、电话卡具体实施行为的判断,即明知的内容和程度上现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采纳“确定性认识说”,认为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要有确定性认识,即不能仅仅主观上认为被帮助对象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还要对可能涉及的罪名、犯罪经过有主观上的认知。第二种观点采纳“概括性认识说”,认为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要求确切、确实地知道,只要具有概括性的认知即可。第三种观点采纳“确定+概括性认识说”,认为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包含确切知道和概括知道两种。
理论上的分歧传导至司法实践领域,在案件具体的认定上就出现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对银行卡、电话卡等实行实名制管理,“卡农”“卡商”出租、出借自己或他人名下银行卡、电话卡时应当具有违法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不再要求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有进一步的明确认知。因此,案例中被告人石某、张某对他人实施网络犯罪具有主观上的明知,但石某具有的是概括明知,可以帮信罪定罪处罚;张某主观上不但具有确切明知,客观上还通过聊天软件每小时向上家报送数字“1”表示一切安全等,综合全部行为可以认定为网络犯罪的共犯。第二种意见认为,对“卡农”“卡商”等主观“明知”的推定应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应当结合一般人的认知水平和行为人的认知能力等进行综合判断,且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案例4中的张某构成网络犯罪的共犯,但案例3中的石某虽然被公安机关教育训诫,不能由此得出其主观上对他人利用电话卡实施犯罪具有确切的明知,故可以帮信罪定罪处罚。
研讨发言——王勇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1.赞成帮信罪独立定罪的观点。帮信罪不是必然的共犯,行为人的明知比共犯中的明知要宽泛。根据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即使帮助犯作为从犯,情节恶劣的也足以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重刑,帮信罪根据立法规定只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帮信罪与网络犯罪的帮助犯是交叉而非完全的包容关系,唯有此才能对立法新增罪名进行合理解释。
2.帮信罪行为人的明知不等同于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中的明知,它包含确切知道和应当知道。对于应当知道,要防止高度倚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认定,也要防止客观归罪,仅以犯罪嫌疑人出售“两卡”行为直接认定。当然,也不能把主观要件的客观化审查等同于客观归罪,二者间有明显区别,帮信罪司法解释和电诈意见二明确规定的多种判断明知的方式,均系用客观事实推定主观故意。
3.帮信罪行为人与网络犯罪共犯的区分。从三个维度进行判断:(1)明知的程度。帮信罪的明知一般是概括明知,指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的犯罪手段、性质、危害结果等都不确定;易言之,就是帮信罪的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可能实施犯罪的“认识内容”和“认识程度”均不明确,只是知道对方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2)对帮信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确切故意,是否认定为网络犯罪的共犯,则需进一步从客观行为进行分析。确切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知的内容明确具体,对被帮助对象的犯罪手段、性质、危害结果等较为清楚。在行为人具有确切明知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审查行为人是否参与了网络犯罪的一些关键环节,审查帮助行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作用大小以及参与程度,这是认定共犯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案例4中的张某利用GOIP设备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群发短信、拨打电话等活动,该行为系上游诈骗犯罪正犯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行为人在收到上家“鱼上钩”信息后会把电话卡拔出,足以推定其主观明知上游实施的系诈骗行为;客观上每隔一个小时就向上家发送信息,提示是否安全,此行为类似网络中的“望风”行为。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上系确切明知,客观上实施了帮助正犯、网络“望风”的多种帮助行为,对行为人可以认定为诈骗共犯。(3)结合行为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综合判断是否达到了罪刑均衡的标准。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诈骗共犯、掩隐罪的关联被告人相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明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可以考虑认定为共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实现罪刑均衡的,认定共犯就要慎重。
赵运锋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1.对帮信罪“明知”的理解与认定,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1)从故意的角度看,帮信罪的明知应该是概括故意中的明知,即对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明知,但该种行为构成何种罪名并不要求。(2)从明知的属性看,明知是一个现实的认识,也是帮信罪行为人的客观认识。(3)从明知的程度看,明知是确定的明知,如果只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怀疑或模糊知道他人可能会实施犯罪,则不能认定为帮信罪中的明知。帮信罪行为人主观明知需要是确定的明知或者是高度盖然性的明知。
2.帮信罪行为人明知的认定方法。依据经验法则和社会常识来推定明知符合司法认知的一般规律。在司法实践中,还需要结合行为人的职业、工作经验以及具体行为等多种因素,对帮信罪行为人的明知进行综合认定。
3.帮信罪与网络犯罪的帮助犯主观要件的区分。第一,两者对犯罪行为认识不同,帮信罪对上游犯罪有概括性认识,不要求对具体罪名有明确认识;帮助犯则要求对共犯行为有确定认识,包括其参与实施的具体罪名;第二,两者对犯罪结果认识不同,帮信罪行为人一般是放任上游犯罪危害结果发生,帮助犯则是希望或者放任共犯行为危害结果发生。第三,就片面共犯而言,依然要求帮助犯对犯罪行为有明确认识,且希望或放任共犯行为危害结果发生,这与帮信罪的主观认识有明显不同。
黄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关于帮信罪的司法适用。近年来帮信犯罪成井喷态势,一定程度存在“口袋”罪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1)对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网络犯罪查证弱化,司法实践中出现查清上游犯罪的定掩隐罪,查不清的定帮信罪的情形;(2)对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宽松,有的案件中行为人在办理银行卡时被提示银行卡不得买卖,由此即推定出行为人主观上的明知,劳东燕教授提出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达到;(3)行为的违法性、不正当性在实际认定中也较为宽泛,将帮信罪的行为涵盖了违法的帮助行为与客观上的中立帮助行为。(4)帮信行为的层级化较为明显,出现了多层次、多链条现象,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哪一层级才是真正的网络犯罪正犯。
2.关于帮信罪的定位。倾向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观点,而非量刑规则。帮信罪是对帮助行为的特别规定,但其帮助行为没有完全独立于被帮助行为而存在,否则背离了本罪处罚的基本原理。据此,认定帮信罪仍然应当以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被查证属实作为前提,或者有证据证明在行为人的帮助下,他人实施了信息网络犯罪。
3.关于帮信罪主观明知的认定。(1)关于“明确知道”还是“可能知道”。刑法中的明知是指明确知道,这是认定主观故意的前提和基础,认为被告人可能知道也构成明知的观点,不符合明知的认定要求。关于“应当知道”实际上是明确知道的一种证明方式的表述,即通过间接证据或推定的方式来证明被告人明确知道,不影响明确知道要求的把握。(2)关于确切知道和概括知道,倾向于同意明确知道和概括知道均属于帮信罪的明知,既可以是行为人对他人所实施的网络犯罪具体类型确切知道,也可以是对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有概括性的认知,无需确知他人究竟实施何种信息网络犯罪。(3)关于事前、事中和事后明知,倾向于同意帮信罪仅包含事前、事中明知,不包含事后明知。帮信罪与掩隐罪的本质区别应当是前者属于事前、事中帮助,而后者系事后隐瞒。实践中提供“两卡”的行为人往往长期多次实施,提供的“两卡”既用于网络诈骗等的收款,又用于网络诈骗等之后的转款,属于一个概括故意下支配的犯罪行为,考虑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帮信罪或掩隐罪一罪处罚,而无需数罪并罚。(4)关于明知的程度,应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对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明知推定,需要严格适用,而且应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
单元总结——周加海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这一专题有高度的共识:第一,帮信罪的明知可以通过推定来认定,推定是一种常见的司法证明方式,并非客观归罪。第二,明知不仅包括确切知道,也包括概括明知;概括明知是不是要限于行为人知道其帮助行为有高度的可能性会被用于网络犯罪,可以进一步研究。第三,明知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审慎把握,不能仅仅以行为人知道“两卡”不能买卖、转让还实施买卖、提供等行为,或者银行办卡时已经提示不能买卖,就认定行为人具有明知。从实践看,转让“两卡”并非一定会用于犯罪,有的可能只是为了规避实名制,而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否认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应当按照司法解释和电诈意见的规定,结合交易方式、交易价格、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有未受过处理等进行综合评判。
三、帮信罪与掩隐罪的界分
【背景材料】
案例5:2020年2月,被告人梁某先后办理三张银行卡及对应的电话卡、支付宝账户后出售给他人,购卡人为防止梁某通过挂失方式转移卡内钱款,在售卡之后十余天内梁某与其他售卡人一起居住在指定宾馆内,购卡人操作手机进行转账时梁某等在一旁,必要时梁某配合刷脸认证。除售卡费用外,购卡人另支付梁某每天200元的费用。经查,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被骗钱款转入梁某账户,后被转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人未被抓获到案。
案例6:被告人邹某在赌场认识了一名叫“阿华”的人,并欠“阿华”2000元赌资。“阿华”提出邹某帮忙开几张银行卡走流水,可无需偿还欠款,邹某遂以自己及家人的名义到银行开设了六张银行卡供“阿华”使用,并在资金入账后按照“阿华”的要求取款。经查,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被骗钱款42万元转入邹某的银行卡内,邹某取款共计41万余元并全部交给了“阿华”指定的领款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人未被抓获到案。
争议焦点
被告人梁某、邹某的行为构成帮信罪还是掩隐罪,抑或同时构成上述两罪?
情况介绍——任素贤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一种意见认为,帮信罪不适用于事后的帮助行为,被帮助对象限于犯罪准备或者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人,掩隐罪发生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既遂之后,对于被帮助对象犯罪既遂之后,行为人实施的帮助转账等行为,应认定为掩隐罪。案例5中的梁某、案例6中的邹某,事前提供了“两卡”,事后参与了转账等行为,对于事前的提供“两卡”行为,构成帮信罪;对于事后的转账行为,则构成掩隐罪,应当予以数罪并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帮信罪中的帮助包括事后帮助,行为人事先提供了“两卡”,事后又帮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应以掩隐罪与帮信罪中处罚较重的罪名处罚,案例5中的梁某、案例6中的邹某事前提供了“两卡”,事后参与了转账等行为,同时构成了帮信罪和掩隐罪,应以处罚较重的掩隐罪定罪处罚。
此外,与之相关的争议问题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认定标准如何把握。有观点认为,就案例5而言,由于“必要时梁某还需配合刷脸认证”,意味着如果梁某不在场,诈骗行为人无法转出资金,故应当认为诈骗行为人没有实际控制资金,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但是,多数观点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与诈骗罪既遂相同,都应当以实际控制财物作为既遂认定标准,对“实际控制财物”不应要求必须“亲手”控制,对于其所控制(组织)的人控制财物的,即可认定为犯罪既遂,故所涉情形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
研讨发言——陈轶群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1.就明知的程度而言,仅单纯提供银行卡的行为人一般只能预见到“两卡”被帮助对象用于网络犯罪的可能性,是或然性的认知而非确定性的认知,可以帮信罪定罪处罚;提供账户并实施转账、取现等行为的人,对于资金性质和犯罪数额往往有更明确的认识,可以定掩隐罪。
2.就支付结算行为的对象而言,掩隐罪的对象只能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行为的对象还可以包括其他和网络犯罪有关的资金,比如帮助诈骗团伙向被害人转账诈骗前期的“返利”资金、支付境外服务器的租赁费用等,这些难以被评价为掩隐罪,以共犯论处又可能罪责刑不适应。在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评价时,应当充分把握帮信罪堵截性、补充性的特征,避免帮信罪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当扩张适用。
3.就本专题两个案例而言,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收益,仍提供账户给他人使用并代为转账、取款,或者为他人转账、取款等提供刷脸验证、协助解冻等帮助的,可以按照掩隐罪定罪处罚,仅提供刷脸验证等帮助的参与者,可以评价为上述犯罪的从犯,以实现罪刑均衡。对于事前提供账户、事后又转移犯罪所得的行为,不宜仅以提供账户的时间节点来区分是正犯的帮助犯还是掩隐罪,还需要对明知程度进行实质分析判断,缺乏客观性证据证明或推定达到共犯明知程度的,即使客观上行为人是在犯罪既遂之前就提供了帮助,仍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以掩隐罪定罪处罚。
高艳东
(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1.帮信罪需要按照“以刑制罪”的观点解释。帮信罪和掩隐罪在客观行为违法程度上存在重大区别,掩隐罪的客观行为违法性更强,需要有“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等积极违法行为,而帮信罪的行为客观违法性较弱,客观行为主要是“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等中立帮助行为,具有一定的业务正当性,客观违法性程度不高。在“两卡”类犯罪案件中,如果行为人只是单纯提供银行卡,未参与转账行为,一般只能认定为帮信罪;如果不仅提供了银行卡,还帮助刷脸转移资金、代为线下取款等,其行为的违法性程度更高,应当认定为更严重的掩隐罪或者共犯。
2.帮信罪的立法定位是补充条文、“备胎”罪名。只有在无法认定为诈骗罪共犯或者掩隐罪等罪名时,才有适用帮信罪的余地,把帮信罪作为打击网络犯罪的主力罪名是本末倒置。司法实践中,如职业化“卡商”以收购、倒卖银行卡为业务,可以按照诈骗罪共犯或其他犯罪处理;对一些仅提供银行卡的大学生,即使对犯罪有概括、模糊的认识,因其未参与资金流转(未动手操作银行卡转账),也不属于“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即仅提供银行卡并不是“支付结算”,对其只能行政处罚。
3.帮信罪不能成为放纵主犯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替代其他犯罪的“口袋”罪。目前司法实务中大量适用帮信罪,打击了很多帮助行为,反而有可能放纵了背后的主犯,不利于真正遏制网络犯罪。同时,大量适用帮信罪,带来“帮信罪膨胀而抑制其他罪名”的效应,原本应按照诈骗罪共犯或者掩隐罪等处理的行为,都被作为帮信罪处理,形成用帮信罪替代其他罪名的反噬效应,应当予以纠正。
喻海松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处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1.帮信罪的实质。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帮信罪的设定缘由,但对帮信罪的把握还需要回到刑法条文本身。从刑法条文来看,帮信罪的规制范围不限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情形,换言之,所涉帮助既可以是事前、事中的帮助行为,也可以是事后的帮助行为。不应以时间节点,而应以行为性质对帮信罪与掩隐罪作出界分。“两卡”案件所涉的单纯提供银行卡的行为,并不属于帮信罪罪状之中的“支付结算”,而应纳入“等帮助”的范畴。正因如此,不赞同把“流水金额”认定为“支付结算金额”,适用司法解释规定的20万元的入罪标准。
2.对于行为人向他人出售、出租银行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在同时符合帮信罪与掩隐罪的前提下(需要注意,掩隐罪限于事后行为,限定于被帮助对象成立犯罪的情形),可以掩隐罪认定。
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售、出租银行卡,未实施其他行为的,可以帮信罪定罪处罚。
4.电诈共犯的适用情形。对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情形,既然已经正犯化,原则上就要适用正犯化后的罪名,即使与正犯之间存在共同犯罪关系。但对于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之事前通谋,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其提供银行卡或者转账取现,甚至参与利益分成的,可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单元总结——周加海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第一,帮信罪的“明知”能否包括事后帮助的明知。帮信罪单独成罪后,刑法第287条之二确实未限定其中“明知”只能是事先、事中帮助的明知,因此,从字面看,认为该条规定中的“明知”也包括事后帮助的明知,并非于法无据。但问题是,这样解释是否合理?从帮信罪的设立背景看,认为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中的“明知”也包括事后帮助的明知,恐怕有失妥当,也会造成帮信罪与掩隐罪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第二,从实践看,提供“两卡”特别是提供银行卡,既有可能是被电诈分子用于在诈骗过程中直接接受被害人转账过来的款项,也有可能是被电诈分子在诈骗得手后用来分流赃款、取现。由于帮信行为人的主观明知通常是概括明知,其并不关心、介意其所提供的银行卡具体被用于哪个阶段,因此,可以按卡的客观用途来确定其行为性质,即卡被电诈分子用于诈骗过程中接受款项的,行为人属于事先、事中提供帮助,应按帮信罪或者诈骗罪共犯论处;卡被电诈分子在诈骗既遂后用于分流从被害人处骗来的款项进而取现的,属于事后帮助,应按掩隐罪论处(当然,反复向同一人提供类似帮助的,需要特别讨论)。这符合概括故意的性质特点,并非客观归罪。
第三,关于提供多张银行卡,有的被用于收取款项、有的被用于分流赃款的处理。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出卖了多张银行卡,无法一一查明银行卡的最终用途。按照卡的用途,分别按帮信罪、掩隐罪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进而实行数罪并罚,存在实务操作上的困难。倾向于认为,对此类案件,可以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指引下,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综合评价,具体而言:综合卡的数量、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行为人获利多少、有无被处理的前科等主客观情节,如果全案按帮信罪处理、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已能恰当评价其社会危害性的,可按帮信罪一罪处理;如果按帮信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罪责刑明显不相适应的,可以考虑定掩隐罪或者是诈骗罪的共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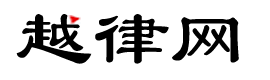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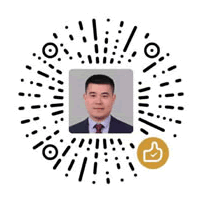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